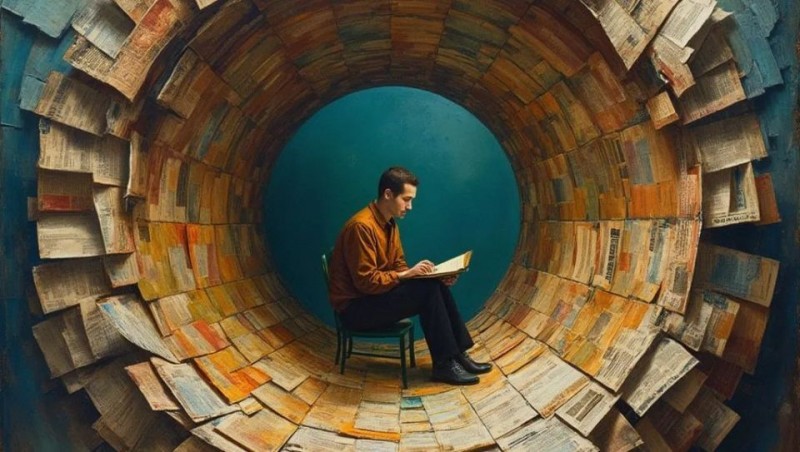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ID:vistaedulab)
内容合作 | 微信号:waitan2022
邮箱:tbeducation@daznet.cn
“老师,我今年看了56本书!”
在2024年的最后几天,北京四中高二年级的一名学生梳理了自己这一年读过的书。这个发生在师生之间的交流,触动了同为高二语文老师的我。
当时,我正在阅读美国作家大卫·丹比的《重燃文学之火》。这本书探讨的是美国高中生的阅读问题。书里提到了许多在我看来是两个国家的学生存在的普遍且共同的现象。比如,美国青少年在17岁时为乐趣而阅读的可能性要低于13岁,因为大多数人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且长时间使用互联网。
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不仅显得微不足道、枯燥乏味”,还显然占据了大把的时间。
与此同时,虽然文字阅读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大多是在电子屏幕上阅读,严肃书籍的阅读量明显下降了。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和身边那个以阅读为乐的学生让我忍不住好奇:
虽然学校和老师常常会给出阅读建议、书单,但是学生私下里是怎么想的呢?
在时间和精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还在自由地阅读课外书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到底读了多少书,读了什么书?
于是,我给自己任教的两个班布置了一项特别的语文作业:制作一份自己的年度书单。

万君
出人意料的书单
很快,33位学生的书单来到了我的手中,寻找答案的旅程就这样开始 了。
这份书单显示出的第一个特点是:考试和老师在高中年龄段的阅读活动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学生读得最多的是《红楼梦》《雷雨》《茶馆》。其中《红楼梦》是整个年级正在推进的考试必读书,而《雷雨》《茶馆》则和课文高度相关。
另外《月亮与六便士》《刘学锴讲唐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长安的荔枝》等书籍,是我曾在语文课上提到过的,因此也进入了学生的书单。
《局外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西西弗的神话》等作品则体现了同伴之间的影响。班级里形成了小范围内同读一本书的风潮。时下流行、书店畅销的书籍也常常出现在其中,比如《悉达多》《外婆的道歉信》。
这份书单显示出的第二个特点是:高中生要比我想象的更重视经典阅读、严肃阅读和学术阅读。
文学经典方面有《莎士比亚戏剧集》《百年孤独》《1984》《巴勃罗·聂鲁达诗集》等;
哲学思想方面有《理想国》《利维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西西弗的神话》等;
学术方面有《经济学原理》《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普通地质学》《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等。
马尔克斯、东野圭吾、加缪、余华、太宰治、曹禺、张爱玲、三毛、王小波是学生中人气较高的作家。
这份书单显示出的第三个特点是:高中生的阅读视野比我想象的更广泛多元、有趣深刻。
年轻人的心,四面八方哪儿都会去:《地下室手记》《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素食者》《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灿烂千阳》《采桑子》《万历十五年》《门德斯传》《读库2401》……
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一股脑儿出现在了他们的书单中。在他们的书单面前,我既为有这样的学生而高兴,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不安。
这份书单显示出的第四个特点是:阅读对他们的影响正在热烈地发生着。文字、书籍与青春碰撞交融,在心灵成长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心爱情,也关注思想
期末原本是一个学生最忙碌的时刻,但许多学生不仅列出了书目,还分别用一句话的方式,写了推荐理由或阅读感受。
学生争先恐后地向我表达着。爱情当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话题。
“在高中,爱情是一种既讳莫如深又无孔不入的事物。我最喜欢《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这句话,如果你过得不幸福,我所做的一切才是徒劳——怎么会有人这样不切实际、不顾一切地希望世界上的一切永存?”
在分享完关于爱情的感受后,这位女生继续列出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北极村童话》和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本巴》:“阅读迟子建和刘亮程的作品时,总有一种淡淡的忧愁。一种岁月慢慢把石头打磨得浑圆的忧愁。一场飓风把马孔多一扫而空的忧愁。一种漫漫黄沙上传来悠远驼铃声的忧愁。”年轻人对情绪的感知正处在最敏锐和丰富的阶段。
与此同时,批判性、独立思考的意识也在他们的书单中有显著的体现。
“阿城的《棋王 树王 孩子王》让我很意外。作者未经雕琢的语言却展现出诗一般的韵律。那段时间,他描绘的王一生整天浮现在我脑中:你有过什么值得为之倾尽一切的热爱之事吗?你现在做的事情,曾给过你直抵灵魂的反馈吗?没有,什么都没有。于是我嫉妒王一生的幸运: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个坚定的锚点,便可以将自己锚定在岸边。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一辈子浑浑噩噩。”高二学生张涵钰这样写道。
他们涉猎广泛,什么都想看一看,以此满足对世界和人心的好奇。
“《第二炉香》是张爱玲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我第一次读后发现确实要用脑子看。我第一次读,说实话没有读懂,只是理解了表层故事,看了一个很长的分析视频后才明白背后讽刺的现象,不寒而栗,让人拍案叫绝。”
“看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么久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消防员瓦西里送给妻子的橘子、小娜塔莎替露德米拉吸收的28伦琴辐射,记得被射杀的小猫小狗和院子里漆黑如墨的铯。”
书单上的书他们没有都看完,没看完就直接标注出来,但喜欢的作品也会特意标注上,“已经刷了3遍”。
还有的同学会顺手写下新年的阅读计划,也有同学表示确实一年来“只读了几本书”,或者是“大部分精力放在了《1984》这一本书上,但以后可以多读一些”。
他们也不会刻意显示自己的“深刻与高深”,比如有学生非常认真地推荐了自己醉心的网络小说《赛博修真十万年》,还有学生真诚地表示正在读的是小学时候就爱看的小说《猫武士》,还有同学非常坦诚地写下了一部显然“超纲”了的《性心理学》。
他们同时还分享着自己的虚荣和失落:“在地铁上,别人都在看手机,没有空座位,我站着,掏出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边开始读,一边观察别人的反应。我的双肩背包里还有一个球拍。但是周围没有异样的眼神,因为他们都不care我。这个时候,我确实觉得生命之轻不能承受。”
西西弗的努力并不悲观
书单作业的批阅过程给我带来近几年职业生涯里一次迥然不同的体验。
我感觉,他们平时鲜有这样强烈的表达欲,正因如此,虽然这不过只是一次以文字形式提交的作业,于我们师生双方而言,却都是一次自由自在、身心舒畅的聊天。
四中高二学生李勃彤用了一年的时间接近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
于他而言,阅读无关乎成绩和学业,而是一种非功利的精神需求。
2024年的12月,在我为学生和阅读之间的关系隐隐感到担忧的时候,李勃彤写下这样的话,告诉我不要为此太过悲观:
我把书单整理完,然后以电子版的形式发给了学生,希望他们相互影响,在新一年中获得一点继续阅读的激励和启发。和我的语文课比起来,来自同龄人之间的陪伴和影响,或许在他们的成长中,才是真正有益和宝贵的部分。
四中历来重视阅读,比如学校推进的师生共读计划,比如高中语文组倾全体之力为学生编选的《澡雪》文丛。语文组坚持每周一次,用上课时间阅读《澡雪》。即便高考在即,也不曾中断。
老师和同学之间,是阅读之路上彼此的陪伴。四中的高杰老师2024年读了50本书,利用碎片时间听书260本。
在她的组织下,2024年12月31日晚上,四中的9位师生和家长举办了一次线上读书分享会,以知识分享的方式辞旧迎新。比如北大元培学院通用人工智能班学生、北京四中2023届毕业生吕俊辰这一年既读了《庄子发微》,也读了《现代性与大屠杀》,还读了《厌女》,非常跨界。
我向来非常确信,从高考写作的角度来看,超越考试的必要条件是丰厚的阅读积累。但我未曾确认的是在课堂和学习之外,压力日增的学生到底和阅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我的书架上至今保留着一本2014年印刷的小册子《北京四中高中书目导读》。早在10年前,我的前辈袁海萍老师就进行了关于高中语文课外阅读导引策略的教育研究,并带领学生列出了一个全面、丰富且有体系的“四中书单”。
当时书单的学生主编之一梁晨在导言中这样写道:“希望学弟学妹在享用这份书单的同时,可以将推荐书目的筛选和增补工作不断地进行下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推荐新出现的、适应学生需要的好书”。
听说我在整理学生的年度书单,现在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四中毕业生陈翔宇也给我发来了他的书目。他说:“高中时,我其实不太喜欢读书。但进入大学后,我对世界有了更多的好奇和疑问,阅读也慢慢成了我寻找答案和排解情绪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里,书籍给了我片刻的宁静。这时的阅读不再是任务,而是我发自内心的选择。或许,阅读的意义就在于此——它让我们的灵魂找到一处归宿。”
大卫·丹比在《重燃文学之火》中问:“现在,还有可能培养出一个不读点‘好的’就活不下去的孩子吗?”
这份以年度书单为话题的作业,给我提供了一份确定的、并不令人沮丧的答案。
来自北京四中学生的年度书单1
高二学生胡杨雅竣
来自北京四中学生的年度书单2
高二学生王茉莉(化名)
来自北京四中学生的年度书单3
2021届北京四中毕业生
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学生
陈翔宇
K12 成长与教育社区
追踪前沿资讯 洞察成长规律
挖掘充满温度的故事 探索融合世界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