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志强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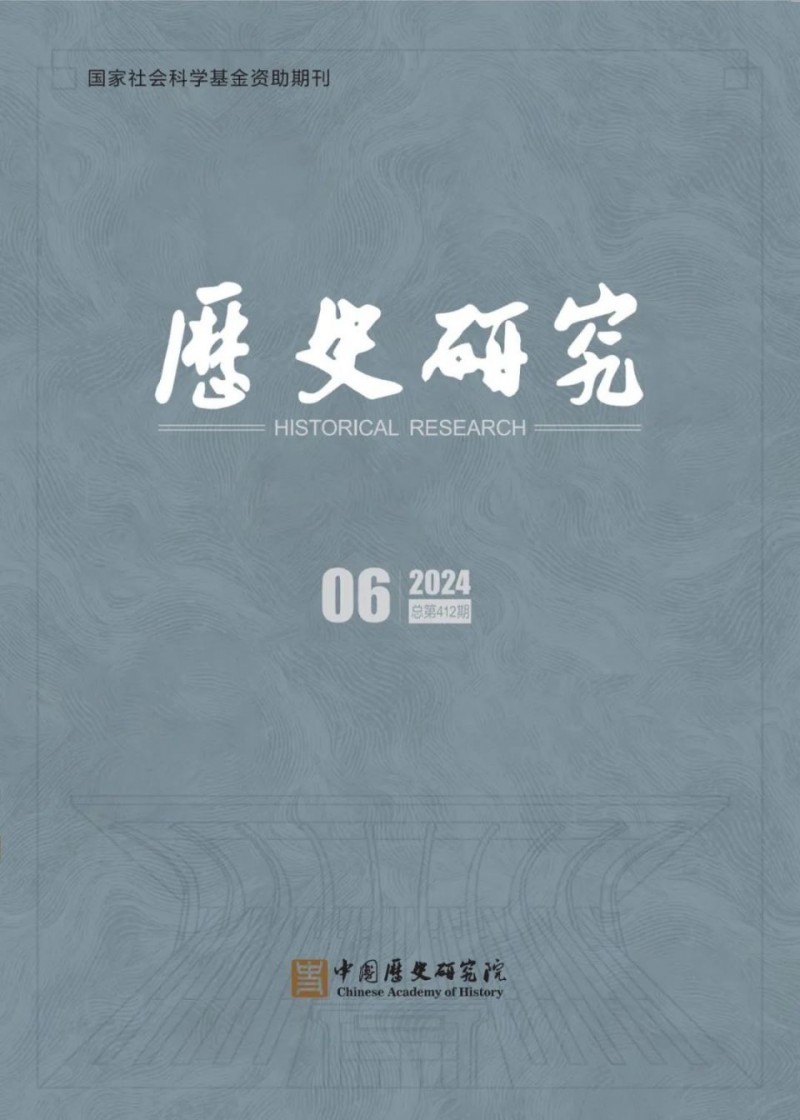
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本框架。与政治世界中的复旧拓新并行的,还有思想世界中国家观念的形塑与变迁——宋明时代人们对于“何为中国”的解释,在容纳广袤边疆地区的清代遭遇重大挑战,亟须更新。对此,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方面还有若干尚未厘清的问题,其中讨论较少的是清代对于天下山川脉络的整理与重述。
大地山河天然存在,但对自然山川的认知,往往和国家边界、地理脉络、人文景观等政治及文化观念纠缠在一起,并不单纯属于客观知识范畴。自《禹贡》至明代,中国逐渐形成一套关于宏观山脉的理论,认为天下山脉起自昆仑,分三条大干进入中原,开枝散叶,形成北至燕山、南至南岭的山脉系统。进入清代,新的统治者来自山海关外,满人发祥地长白山并不是中原士人熟知的名山,而且西域、西藏、蒙古等地面积广阔、地形多样,分布着许多大山大水,它们与中原地区真实地理的关系和宇宙论联系都有待梳理。此外,清初一些遗民将中原地区与政治正统联系起来,试图将“华夷之辨”固定为地理空间的划分。在此背景下,清代以《一统志》《皇舆全览图》和《西域图志》为代表的官方地理学、在考据学脉络中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乃至风水观念支配下的堪舆地理学,都各有应对,创造出适应拥有广阔疆域与多元族群的新王朝的天下山川新脉络理论。
ntent="t">一、《皇舆全览图》与康熙君臣关于泰山的讨论
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开始编纂搁置了十数年的《一统志》,正式开启整理与重构天下地理知识的进程。此后,对全国地理情况的调查测量旷日持久,而在宏观山川脉络方面首先引起朝野关注的,是如何处理泰山在文化地理版图中的地位。
诸多名山中,泰山的位置极为特殊。一方面,泰山是五岳之尊、名山之长,在古代中国的地理格局和信仰世界中地位独特,特别是孔孟都生于泰山左近,泰山因此成为人文地理尤其是堪舆地理学中被持续讨论的对象。另一方面,从自然地理角度看,泰山独起于东方,与太行山、秦岭等人们熟悉的中原巨大山脉皆无关联,不易纳入以想象的昆仑为中心的中国山脉系统。如元代金履祥将天下山脉分为“三络”,却不得不将泰山置于“三络”之外,称“惟泰山则特起东方,横亘左右,以障中原”。明代风水师和地理学者则发明出“伏地潜行”、“脉乱于河”等说法,试图将泰山与秦岭连接起来,但毕竟是强为之言,真实世界的山川地理与理想化的堪舆格局之间,始终存在无法相合之处。
清代皇权对传统山脉理论的重塑,就从泰山的“来脉”入手。《清实录》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载:
康熙帝《几暇格物编》收有《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是他关于此事的正式表达。康熙帝先批评了两家学说:一是“古今论九州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该说法来自朱熹,是以风水世界观描述的中原地理大形势;二是“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是前引金履祥之说,为《人子须知》等风水书所继承。康熙帝则称“细考形势,深究地络,遣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具体论证是:长白山为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之源,其南麓分为二干,一干往西南,东至鸭绿,西至通加(今名浑江),“高丽诸山皆其支裔”;另一干自西而北,“至纳禄窝集复分二支,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业山,折西为医巫闾山。西支入兴京门,为开运山,蜿蜒而南,磅礴起顿,峦岭重叠,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而龙脊时伏时现,海中皇成、鼍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其中,天柱山是清太祖福陵所在,隆业山是清太宗昭陵所在;开运山即启运山,清朝祖陵永陵所在。长白山与泰山中隔渤海,康熙帝引用风水理论,以“今风水家有过峡,有界水。渤海者,泰山之大过峡耳”进行解释。再者,泰山面西北而背东南,“若云自函谷而尽泰山,岂有龙从西来而面反西向乎?”
在康熙帝的描述中,长白山与传统认知中的三条大干都无关,是一座独立发脉的神山。以这一新晋神山为中心,康熙帝打破天下诸山皆源自昆仑的共识,构造了一套全新的山脉系统,脉络涵盖东岳泰山及北镇医巫闾山,而且结局为盛京、兴京及入关前的皇陵,相当于满洲兴起的堪舆依据,与以昆仑山为中心、布满华夏的《禹贡》式山脉系统东西对峙,天下山脉隐然变成一个双中心的系统。《清圣祖实录》终卷列举康熙帝在知识上的十项贡献,“泰山为长白之分支”居其一,足见这一说法并非其偶尔好奇。
面对皇帝的提问,李光地只能以他所了解的传统山脉说回答,即泰山属于三条大干中的“中干”,乃秦岭余脉。康熙帝既已谕示泰山山脉来自长白山,李光地自然要表示心悦诚服,但在这段对话之后,李光地写下《上谕泰山脉络恭纪》,表达了另外一种看法。他寻经绎史,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即青、兖、徐、扬,江、浙、闽、广之山,均不在《禹贡》“四条”之内,由此认为“《禹贡》四条之山,但以中原脉络可见者言之耳,北不逾塞垣,南不逾岭徼”,即北不过长城、南不到南岭。但是另外有两条山脉,发源于《禹贡》九州之外而环绕中原:北面一支是长白—泰山之脉,“自塞外横海而来,自登、莱以尽于青、徐”;南面一支是江、浙、闽、广之脉,“皆自岭外回环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岭分支,南尽于闽、广而北尽于江、浙”,这两条“塞岭以外之山”乃天作地成,“以为中原之左右藩护”。李光地承认康熙帝所说泰山山脉自塞外而来,却回避了长白山及盛京、兴京、皇陵等堪舆要素,而且发明出一套更宏阔的山脉系统,使这条结成泰山的巨大山脉成为中原“藩护”,既容纳了中原之外的王朝圣山,又维护了中原在堪舆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天下之山皆源自昆仑的传统看法,事实上委婉否认了长白山单独发脉。
随着测量活动铺开,相应的地图也陆续绘出,送至内廷后,再校正、拼合为全国总图,后世统称为《皇舆全览图》。《皇舆全览图》版本众多,其中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个版本中,分别以红线、黄线绘出南北两条大干。一个较早的刻本显示,南干起自昆仑山东南,顺金沙江南下,经云、贵、湘、赣等省入闽,至福州入海;北干起自昆仑山之东北,经星宿海、陕甘、蒙古,出义屯门(今长春),经兴京至长白山止。另一个较晚刻本中,北干在长白山之后继续南行,贯穿朝鲜半岛入海。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康熙帝谕内阁学士蒋廷锡,令其将《皇舆全览图》并分省之图与九卿细看,不久九卿回奏,称颂《皇舆全览图》有“从来舆图所未有”的四个特征,其中第二条即南北两大干:“一干自昆仑东北,历西番境,至兴安岭,达于盛京,南折入朝鲜境入海;一干自昆仑东南,历云、贵、广西、湖广、江西境,或东或北,折至闽、浙入海……从来舆图所未有也。”得到九卿的回奏,康熙帝才谕示“图着颁发”。据这段君臣对答,九卿看到的应即此较晚刻本的底本。九卿覆奏并称,“凡两干以南以北之水,大则名川灵渎,小则泉涧溪潭,莫不顺山脉以分流,随地形而转下,萦回盘带,刻镂绣错,而寻源溯委、条贯井然”,说明南北两大干应系以分水为原则。目前已公布的《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六年刻本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南北两大干基本沿分水岭绘出:红线(南大干)以内为长江水系(以岷江为江源)、钱塘江水系,澜沧江、怒江、红河、珠江及闽浙诸水系则在红线以外;黄线(北大干)西半部将黄河、海河水系划入线内,东半部较为模糊。根据九卿的描述可知,辽河水系当在黄线以内,松花江—黑龙江水系则在黄线以外。
《皇舆全览图》大体以分水岭为大干,体现了测绘技术的应用,但大干走向及线内线外之分,则受制于中国传统观念与清朝皇权地理,是对明代干龙理论的正面回应。新的山脉论一方面强调长白山、兴京在堪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不但历代名都如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远离南北两大干,甚至连北京也不能与满人发祥地东北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将东北诸山重新纳入以昆仑为中心的天下山脉系统中。此外,泰山不在大干之上,也隐然降低了泰山的地位。康熙帝令九卿阅看《皇舆全览图》的上谕称,此图“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其实按新法绘制的地图与《禹贡》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康熙帝有意更新作为社会共识的三大干龙山脉系统,弱化南干、取消中干、重构北干,构建起适应清王朝的新皇权地理学。
《皇舆全览图》的南北两大干系何人所绘,目前尚缺乏史料作进一步讨论,但肯定不是参与测绘的传教士独立决定。其实,相较于学界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重视,清代官方史料中留下的记录相当有限。康熙帝、李光地的文章及前引九卿覆奏是当时仅有的公开讨论,都集中在新的山脉理论之上。
有限的文献证据之外,地图上留下了更多线索。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套分省分地区彩绘地图,其底本或即康熙五十八年版《皇舆全览图》刻本的底图,底本绘制时间不晚于康熙六十一年。这套图部分地区附有文字图注,内容以天文次度、分野、四至和山川形势为主,其中,山川走向往往被重点关注。如《江南全图》称“长江盘绕于中脉,自广信走徽至苏,尽于江阴”,“江之北属中干,江之南属南干,是省山水大聚,声名、文物、货财、赋税遂压天下”,浙江、云南、四川等图莫不如是。描述不厌其详,内容大略同于经典的三大干龙理论,不会是测绘结果的客观体现,只能是中国传统地理观念的主观表达,也颇能体现时人关注所在。
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山东全图》如此描述泰山来脉:“山脉源于中干,从开封而走青、齐,尽于登、莱;黄河夹北,长江夹南,邹、鲁钟泰山东岳之灵,圣贤出焉。”传教士对山东的测绘在康熙五十年,已在康熙帝与李光地关于泰山龙脉的那场对话两年之后,《山东全图》的绘制不会早于此时,但图注仍然明指泰山源自中干,暗示康熙君臣在新山脉论的构建上尚未取得一致。
ntent="t">二、地理新知与天下山川脉络的重构困境
在原本的山脉系统中,作为万山之祖、世界中心的昆仑山往往只是一种象征性神话符号。尽管历代都不乏关于昆仑究竟何在的争论乃至探查,但纸面的考据论证与零星的实地考察都无法动摇传统世界观,更谈不上重建天下地理图景。然而,康熙朝这次地理大测绘,尤其是对蒙古、西域、青藏等地的实测,促使人们必须将传说地理落实为真实的山川。康熙四十三年,清廷派内阁侍读舒兰、侍卫拉锡到黄河源头星宿海一带勘察,他们回报称“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不可胜数。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即昆仑也”,是以星宿海一带之山为昆仑。在绘有南北两大干的两个版本《皇舆全览图》中,作为两大干共同起点的昆仑,被确切标定在星宿海附近,仍合乎黄河出于昆仑的传统观念。
限于当时局势,《皇舆全览图》未能包含西域和西藏的全部地域,已绘出的西藏部分也较简略。康熙五十六年,清廷派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前往西藏测绘,测绘使康熙帝重新定义了天下山脉之根。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皇帝在给大学士、九卿等的上谕中详细描述黄河、长江、澜沧江、恒河等的源流,并称:“梵书言四大水出于阿耨达山,山下有阿耨达池,以今考之,意即冈底斯是。唐古特称冈底斯者,犹云众山水之根,与释典之言相合。”乾隆九年《大清一统志》记录这次测绘称,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并据此描绘以冈底斯山为中心的天下山脉系统:冈底斯山向西北分出一支为葱岭,东北一支到达陕西、西宁等处,向西南者入印度,向东南者至云南、四川之境。
如果同时承认昆仑中心论和佛教世界观,那么既然天下山脉皆起自冈底斯山,则冈底斯山即传说中的昆仑为合乎逻辑的推论。西北史地学家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说,“昆仑之与冈底斯,又古今之易号”;曾作《蒙古游牧记》、同样关注西北史地的学者张穆作《昆仑虚异同考》,梳理关于昆仑所在的五种看法,结论也是昆仑即冈底斯山,天山、于阗南山都源自此山。然而若以冈底斯山为昆仑、为“众山水之根”、“众山之脉所由起”,《皇舆全览图》所绘从星宿海之昆仑出发的南北两大干就不能成立。
因此,南北两大干理论最终昙花一现。在目前已知的资料中,画有红、黄两条干线的《皇舆全览图》仅有前述两个深藏宫中的版本,后来流传的各版本,包括作为正式版本的康熙五十八年铜版,均未标示南北两大干。无论是有关天下地理的官私著作,还是谈及龙脉的风水书,都难见引述的例证,就连乾隆帝吟咏明陵山川形势的《哀明陵三十韵》,也遵循传统的三龙说,称“太行龙脉西南来”,适合新王朝的山脉系统理论尚未形成。
即便是康熙帝的“泰山源自长白山”说,也得到不同回应。康熙帝《几暇格物编》首刊于雍正十年(1732),此后官私文献中不乏以“泰山龙脉”的名目援引《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的例证,但是,公开表达异议的人也相当多。四库馆臣、山东历城人周书昌对“《山东通志》谓泰山越海而来、与《撼龙》之说异”感到疑惑,致书文字学家、山东曲阜人桂馥,请他旅行时实地考察。桂馥“自陕而东,自徐而北,凡大龙经行河南、山东之地皆得游览”,认为“龙自河南东境折而北,将起沂州诸山,先伏于凤、徐,故黄河得由吕梁穿过。此等大干,水不能劫……龙入山东有分水三,一为峄之阴平岭,二为泗水之陪尾,三为莱芜之原山,过此三峡则东岳插天矣”。魏源同意他的看法,并称“后世黄河横决,而南运河复横截而北,使人忘其所自,至有岱脉自辽东渡海而来之说”,其实《禹贡》所说“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已经尽包中条之脉络,陪尾即泰山之来脉,“至于陪尾”即至泰山。
桂馥、魏源等人的看法是对山脉走向的客观考察,并未涉及王朝合法性的政治议题,但不惮于触碰敏感定都问题的也不乏其人。雍正四年《博雅备考》称,“凡河北诸山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而来……为太行、为恒岳,而东为岱岳”,书中不谈长白山、辽东,只对北京的风水形势大加渲染,重复“泰山为龙、华山为虎、嵩山为案,左环沧海、右拥太行”之类的老话。编者张彦琦评论称,“天下地脉皆发自昆仑,向中国来者三支,其北络折而东南行,背为北狄,正结于冀都,又结于燕京,其支结为辽东……自河徙而南,王气泄矣,正干衰千有余年,而气移于燕京,遂为帝王之都焉”。关于中龙,张彦琦认为其“正结长安”,又强调“洛阳天下之中”,“其气脉大尽钟于泰山,翻身顾祖,东海外护,江河前向,圣人出而英贤萃,其天地中正之气所凝乎?”他大胆主张:“三干龙所为分支劈脉为帝王都者,其气皆已发泄,各享其盛矣,中干之龙犹有未尽露者,其为襄、邓之间乎?”这样的思考当然并无根据,只能说是政治玄学兴趣使然。
一些有机会参与测绘工作的人士,同样在思考天下山川脉络问题。乾隆二十九年,侍卫苏宁阿被派往西域测绘。苏宁阿笃信风水,相信“三大干入中国之说”,但他到过喀什以西边界外400余里之地,又曾向宗教人士请教,得来一些中亚地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想象。其后他绘制《万里回疆图》,图前题词《山川影》专门叙述他耳闻目睹的山脉走向。《山川影》认为,默克(麦加)是位于世界中心的神山:“西方大极之山名默克,环以弱水,不能渡越……回部西域之山,皆来自默克,即番经梵语须弥山、儒书地经昆仑山也。”
在苏宁阿的描述中,山脉自默克发源,然后由西而东,经温都斯坦来到西域,先结霍汉(浩罕)、伊犁,一条向东北方进入俄罗斯,为北海沿边之龙;一条向东,开都河、西域回部诸河、罗卜脑尔湖(罗布泊)、黄河界其南,伊犁江、精河、呼吗哪嘶河(玛纳斯河)、厄勒起思河(额尔齐斯河)界其北,是北大干龙。北大干龙穿越戈壁继续向东,经过宁夏,沿河套过山西,由燕云入木兰(木兰围场,在今承德),东行至渤海,“约二万余里通长白山”。长白山“上有灵池,下多神泉,云雾蒸翳,莫窥其形象,真天地钟灵,乾坤毓秀,赞阴阳、佐化育,为海内东昆仑者也”。
苏宁阿没有提及康熙帝的“泰山龙脉”论,但“东昆仑”一词无疑呼应了清朝对天下山川脉络的重新整理。不过与长白山单独发脉的看法不同,苏宁阿仍将其视作单一中心的天下山川系统的一部分。苏宁阿的地理知识来源多元、虚实相杂,反映了西域疆土纳入清朝版图对国人世界观的冲击和改变,不过,这幅《万里回疆图》并未刊布,仅藏于苏宁阿家中。他的诗文集所收关于西域地理的文字,更接近传统的山脉论,未提及“默克”或“东昆仑”。《万里回疆图》中“默克龙脉”论没有回响。
明亡清兴也给风水师带来新的难题,刊于康熙五十二年的沈镐《六圃沈新周先生地学》就对如何描述北龙相当纠结。沈镐首先将西藏南部的高大山脉视作南、中两条干龙的枢纽,但南龙、中龙皆有明确界线,唯北龙以北未明:“北干其南则黄河,北则沙漠,而自古舆图不载沙漠之所止,其东宜止于东洋,而自辽以北,亦不知东洋之所在。漠北更有北山,北山之后,宜是北海,而宦客泊商,无能至北海者,塞内所得北干,才十分之一。”他之所以强调北干之大,是因为“自古圣神,多生北干”,“本朝列圣陵寝、两京畿辅,皆在北干”。但沈镐对辽东之山完全没有认识,只说北干“委蛇井、代中,复北出高柳,循塞垣南转为京师”。《六圃沈新周先生地学》收有6幅干龙地图,每两幅拼成一条干龙,是目前所见最详尽的天下龙脉图,图中也只在辽东盛京后面象征性地画了三重祖山,孤悬北干之外,表明当时东北地理尚未为中原风水师所熟知。
王朝更迭也给风水师提供了讨论空间。清初著名风水师张九仪公开否认三大干龙理论与明代三都的互证关系,甚至批判《人子须知》作者、明代著名风水师徐氏兄弟“违情背理、阿谀明朝”。他重提朱熹关于太行山脉走向的理论,贬低北京风水形势,认为“北龙从西北转向南行,左股辽东在边徼,中股燕地,僻处直省之东北角,均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势”,特别是北京一带,“上手西山雄峙一方,层峦叠嶂,向南直奔,并不回头营抱;下手通、永,皆平原旷野,无崇山峻岭推出水口以作下开。如此形势,上重下轻,所以辽、金与元历数甚短促,明季稍长,究亦皆一败不能复兴”,认为只有右股山西堪为建都之地。他甚至将中国形势想象为右手覆掌之形,掌心在西北,向东伸出五根手指,太行山为大拇指由南至北,秦岭向东至河南为食指,南龙为中指,云、贵、广西等处之山为无名指、小指,如此则辽东、北京皆在拇指之外,山西地当虎口,当然是形胜所在。无论是山脉走向还是建都之地,他的看法都透着朱熹的影子,对建都辽东和北京的否定堪称大胆。
从皇帝到风水师、从官员到学者,在天下山川脉络问题上歧见迭出、莫衷一是,既是王朝疆域、地理测绘与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足以说明广阔国土对地理观念的冲击之大、新理论需求之亟。
ntent="t">三、清代西北史地之学与天下山川新脉络
清朝收复台湾后有一则传说,称朱熹曾登福州鼓山占地脉,断言“龙渡沧海,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台湾也成为龙脉覆盖之地,是山脉系统随着国家政区增加而扩展的实例,同时也说明山脉理论在国土观念变迁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当西域、西藏等地纳入清朝版图后,如何将这些疆土与中原地区整合进统一的世界观中,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构造清王朝各部分疆域山脉之间的联系,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康熙朝绘制《皇舆全览图》时未能测绘哈密以西地区,因此乾隆九年《大清一统志》并未指明中原诸山与西藏、西域山脉的关系,完成该任务的是乾隆年间编纂的《西域图志》。
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定准噶尔,次年乾隆帝即命人开展西域地区的地理测绘,着手编纂《西域图志》。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测绘范围随之扩展到南疆,苏宁阿参与的即是此次测绘。西域测绘结果体现在乾隆二十一年始撰、乾隆四十七年完成的《西域图志》。它以实地测绘为据,记录西域诸山脉络,又有《西域山脉图》及《图说》概括全貌。与苏宁阿的个人思考不同,《西域图志》遵循《大清一统志》的说法,仍以冈底斯山为天下山脉发源之所,并将西域之山描述成连接西藏与中原北部诸山的中间环节:冈底斯山分出一支向西北为葱岭,葱岭又分出两支,南面一支从于阗南山一直到祁连山、秦岭、华山,即唐代一行所谓“北戒”;北面一支为天山,天山又分出一支向北为阿尔泰山,阿尔泰山再分出四支,向北一支入俄罗斯,其余三支向东,为漠北诸山。因此,“推究西域山脉,断以西藏之冈底斯为来龙,以中土之北戒诸山、漠北之阿勒坦诸山为南北两大山之支干,经络方隅,井然明辨……俾世之谈堪舆者有所考”。阿勒坦山即阿尔泰山,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记其“绵亘二千余里,高入霄汉,盛夏积雪不消,为西北诸山之祖”,并称阿尔泰山共分为四支,发散四方。这段话被《蒙古游牧记》《圣武记》《朔方备乘》等引用,作为重新构造山脉系统的权威表述。《西域图志》扩展了堪舆地理学的覆盖范围,将西藏、西域、漠北和中原的山脉连成一体。
山脉系统整理对《西域图志》有特殊重要性。《西域图志》初修时本有“分野”一门,但因分野之法“不及九州之外……既数有所穷,亦理原难据”,因此在定本中被替换为“晷度”(经纬度)。在天文领域,诞生于中原地区的分野学说无法涵盖辽阔的西部边疆,而在地理层面,联结中原与边疆的新山脉系统及时填补了这项空白,成为中原与边疆之间天然联系的宇宙论证明。以《西域图志》为标志,清朝官方承认、适应于广阔国土的山脉系统终于建立起来,即将天下中心定位在冈底斯山,西域、漠北、中原之山都是这套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个版本的山脉系统中,西藏和佛教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冈底斯山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狮泉河、象泉河、马泉河、孔雀河均发源于此,而狮泉河、象泉河、孔雀河均汇入恒河,是佛教世界观中至为重要的地理标志。但是,黄河、长江却与冈底斯山无涉,按照众山之祖即大水之源的传统世界观,无形中降低了黄河、长江的等级。齐召南曾作出回应,其《水道提纲》称金沙江源出西藏卫地之巴萨通拉木山东麓,该山“山形高大,类乳牛,即古犁石山也”,注云“山脉自冈底斯山蜿蜒而东,至此为诸山祖”。黄河则源出星宿海之西、巴颜喀喇山之东,《水道提纲》称“巴颜喀喇山即古昆仑山,其脉西自金沙江源犁石山蜿蜒东来,结为此山,以地势极高,为南北诸山之祖源……又名库尔坤,即昆仑转音也”,又称星宿海之北有阿克塔其钦山、东北有巴尔布哈山,皆名库尔坤,“三山皆昆仑也”。如此形成冈底斯山—巴萨通拉木山/犁石山(长江源)—巴颜喀喇山/昆仑山(黄河源)的山川系统,不但勾连起新知识与古地名,也证明黄河、长江间接源于冈底斯山。
道光朝以后,一些士人吸收了官方的边疆地理信息,同时接触到域外地理知识,更有一些学人身经目验,开始在更广阔的地理格局中看待中国山川。他们呼应清王朝广阔疆域的政治现实,对天下山川大势极为关心。许多学者同属于影响巨大的西北史地学派,新的地理知识沿着学者的社交网络传播开来。最能引起时人兴趣的,是关于西域、西藏等西部地区的山脉及地处漠北的“真正”北干的看法。在这方面,对晚清知识界影响最大的是魏源。
魏源《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编写的较早全面概述世界地理与历史的著作。在总述世界地理大势的部分,魏源写道:“今欧罗巴、利未亚之山,皆发脉葱岭,逦迤而尽于西海”。利未亚指北非,西海即大西洋,如此整个欧亚非大陆之山脉皆源于中国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同卷《释昆仑》上下篇中,他反对康熙朝测绘时关于冈底斯山乃“众山水之根”的观点,主张以葱岭为昆仑,葱岭“据大地之中,当万国孔道”,“以万山之祖当万国之中”,为“众山太祖”,所以清朝“声教所讫,亦以葱岭为断”,因为那是“天地大气之自为界限”。他吸收艾儒略《职方外纪》及南怀仁《坤舆图说》描绘的世界名山,在三大干龙说及清朝官方山脉学说基础上,整理了一套以葱岭为中心的山脉系统:
咸丰年间,致力于西北史地之学的何秋涛完成关于清朝北部边疆与俄罗斯史地的作品,后被咸丰帝赐名为《朔方备乘》。鉴于传统的北戒或北龙仅及于燕山一带,对于更北的山脉茫昧无考,该书专设一卷《北徼山脉考》,以中国传统的山脉观念描述亚洲北部群山。在他看来,“昆仑大干包瀚海之外……北戒仅可谓之中干耳”,因此必须先明了俄罗斯诸山脉络,方能真正理解中国山川形势。何秋涛说,“阿尔泰诸山乃中国名峤,而支干所分,实为俄罗斯国众山之祖”,位于中俄交界地带的西金山(杭爱山脉)、东金山(金阿林,即小兴安岭)、外兴安岭等“均为昆仑东北干”。魏源认为乌拉岭(乌拉尔山)“为葱岭北干,即昆仑之西北一支”,何秋涛则主张乌拉岭以北的里弗依山(又译大不里山、香山)为葱岭北干。《北徼山脉考》卷末附有《阿尔泰山正干分支总论》,多引魏源之说,分梳天山至蒙古高原及俄罗斯诸山脉络。何秋涛关于俄罗斯诸山脉络的说法虽然详尽,但文中多用“祖山”、“少祖”、“支干”等堪舆术语,实出于中国传统世界观,无怪乎清末有人诧异,“问之俄人,则多未知”,一语道出中外地理知识背后的观念差异。
在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中,堪舆地理学成为学者理解天下山川大势、重构山脉理论的重要资源。堪舆术经典《撼龙经》有关于中国域外形势的叙述:“西北崆峒数万程,东入三韩隔杳冥,惟有南龙入中国,胎宗孕祖来奇特”。这段脱胎于佛教四大部洲理论的原始龙脉论,成为魏源等晚清西北史地学者接受地理新知的基础。李文田为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同时也是风水爱好者,他甚至以地理学知识详细注释了《撼龙经》,将经文中提及的地名一一考证落实,成为堪舆文献“地理学化”的集大成者。
西北史地学者发展出的涵盖清代全部国土的新山脉论,在知识阶层中流传很广。如陈虬论西北水利,主张因山势以通新河,立论基础就是新山脉论。梁启超1901年所著《中国史叙论》,于“地势”一节也首举葱岭为“诸大山脉之本干”、葱岭向东衍为三派,中间为昆仑山脉,“为一国之主干”,蔓延全国。在这一潮流中,李诚所作60卷《万山纲目》(刊于1899—1900年)堪称集大成之作。他认为大漠以南诸山皆起自冈底斯山,大漠以北诸山皆起自阿尔泰山,漠南诸山又可分西支、北大干、东大干、东南大干,东南大干又分出中原中大干、中原南大干,其中北大干、中原中大干、中原南大干大致近于明人的三大干龙说。《万山纲目》虽然也承认长白山为“神圣发祥之地”,但其在整个山脉系统中并无特殊地位,也是从北大干分支而来。无论是李诚,还是《西域图志》、魏源、何秋涛,他们的新山脉论都重在新疆、青藏,中原诸山甚至长白山仅处于下游与从属地位,国土观念在新的山脉系统中得到更新与重建。
清代西北史地学者的新山脉论,重点不在于论证北京或盛京等政治中心的堪舆学地位,而更接近国土论证学说,同时也因为边疆危机的出现而染上地缘政治论色彩。在作于咸丰二年(1852)的《海国图志》“后叙”中,魏源交代编纂《海国图志》的动机,在于对利玛窦等西人所述西洋舆地之学的不满,因为这些著作多详于土产、商埠、天时,但“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则未之尝闻。重视山川脉络、历史沿革是中国舆地学的传统,在魏源的表述中,固然有对“天地气运”的关心,但更出于“悉其形势,则知其控驭”的政治目的。清末留学日本的谷思慎作《蒙古山脉志》3卷,分述帕米尔、天山山系、昆仑山系,重点全在西域,通过山脉系统将蒙古、东北地区与新疆联为整体。弁言中将此书与张穆《蒙古游牧记》进行比较,称不同于张穆的“以方域系山川”,《蒙古山脉志》“以山川定方域”,“有大地河山终古不改之气象”,以自然地理为国家疆域之论证,在愈演愈烈的边疆危机中自然可以发挥作用,如“不龟手之药”,可用之以胜强敌。
“以山川定方域”,山川既可以是边界,也可以是脉络。光绪三十一年,原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谪戍新疆,对山川脉络多有观察思考。他以“葱岭为本,天山为干,燕、晋、秦、陇、蜀、滇诸山皆枝叶”,又说“葱岭为父,天山为母,五岳为宗子”,甚至称“天山无雪,则中原万山枯焦”,正是对清代新山脉论下国家有机体的理解,这个有机体的首要之地自然就是葱岭、天山所在的西域。
裴景福如此重视西域,更直接的原因是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他极为关注英俄在中亚的争霸活动,强调必须经营新疆,才能避免“万一为人所有,则长驱直入,高屋建瓴”的灾难后果。新疆的重要性首先源于新疆之山,所谓“昆仑为五大洲之冠冕,尤为亚细亚一洲之初祖”,至称帕米尔高原上的“大龙池当五洲王气,非类居之,我固可危,俄亦非计也”。裴景福明确表达了地理的稳定性及其决定性地位,“古今事变不同,而山川形势未之或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陆中心的重要性,“今日五洲战事,多在海面,将来各洲,铁路完备,又不在海而在陆矣”,主张“经营五大洲,亦当于山海隔阂限制之处,求其联络贯通”,说的正是以葱岭为中心的中亚地带。几乎同时,1904年,西方地缘政治学奠基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主张地理比人文因素更接近于稳定不变,强调远离海洋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枢纽地位。中西两种不同的观念系统却产生极为相似的理论,裴景福提出的可谓是一种中国式的地缘政治论。
裴景福还受命参与编写《新疆图志》,并负责撰写《山脉志》等卷的初稿。不久裴景福赦还,《山脉志》由王树枏改定后编入《新疆图志》,后又以《新疆山脉图志》之名单独刊行。其中如以葱岭为欧亚东西之脊、龙池即喀喇库勒之类,皆与裴景福说法相同。《新疆图志》多记山水,《山脉志》大量引用中俄勘界文献,首要目的在于厘定领土范围,保护国家疆域。
将西域为中心的山脉系统扩展至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想法在近代相当普遍。如谢维岳辑《中道全书》,其中“地理门”的山脉部分就包括了葱岭山祖、江南山干、河南山干、河北山干、漠北山干、岭前山干、岭后山干、岭西右干、岭西左干、美洲山干、澳洲山干诸条。作者认为,葱岭“居大陆东西南北之中心点,山脉四出”,葱岭往东北为天山,系漠北山干;往东为昆仑,再分三大支,即中国三龙;葱岭正南为印度山干,往西北为乌拉尔山干,往正西为欧非山干。谢维岳在为《中道全书》“地理门”所加按语中称,“东半球之山,葱岭为始祖,诸干为旁支;西半球之山,罗基为主脑,安第为后身,皆一派相承,脉络贯通”。《中道全书》刻于宣统二年,当时清朝已日薄西山,可编者却幻想帮助“圣帝明王宅中国、治五洲,万国归于大同”,“万国大同”始于世界整体论,而地理上的“一派相承”,正是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表征。
更著名的例子是廖平,他重拾“大九州”理论,并将其嫁接在当时所知的世界地理知识上。他主张儒家经典中的天下地理并不限于中国,而是全球地理,批评把葱岭认作昆仑、当成大地之中的观念,说“葱岭为亚洲最高之山,是乃亚洲之中,非天中也”,认为中国只不过是九州中的豫州,“其余八州分布地球”,《禹贡》中大禹所导之山水是全球之山水,如所谓岷山指的就是美洲之山。在此观念主导下,他以经学的方式注解《撼龙经》,将“须弥山是天地骨”理解为“今印度北高原”,将“西北空峒数万程”之“西北”理解为“全球之西北”,即“北美”,“欧洲之脉渡地中海而为非洲,南洋群岛接连澳洲”。因为泰山地近曲阜,所以最为廖平所关注,他主张昆仑之脉东至山东曹州而止,而“泰山脉系从美洲西来渡海……来脉结作孔林,为全球第一大地”,“东西合并,乃笃生至圣,此为全球有一无二之地,帝王京都不如也”。东西半球山脉的分界线在山东之黄河,泰山、曲阜正是东西交汇之地,也就是“天中”。所谓“泰山山脉源自美洲”,是康熙泰山龙脉论的奇异展开,即通过白令海峡,将泰山、长白山与落基山脉连到一起。这种异想天开的“全球山脉论”是廖平将儒学世界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他想象中的全球儒学乌托邦的地理基础。
清朝官方和地理学者关于中国西部的地理知识远超前代。就山脉学说而言,知识的获取、整理与传播固然不乏纯粹兴趣的驱动,但真正主导知识世界扩展的,还是有关国家构建的思想和观念。不同时期,这些思想观念的重心有所不同:在清前期,官方组织了大规模的测绘活动,地理知识如何服务于树立政权合法性是朝野关注的重心;到清中期,西北史地之学兴起,地理因素如何参与国家认同是这些学者努力的目标;在清末,人们的地理视野扩展到全球,地理想象如何帮助确认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又成了时代课题。
ntent="t">结ntent="t"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transparent;background-color:rgb(214, 168, 65);color:rgb(255, 255, 255);font-size:18px;letter-spacing:1.5px;outline:0px;text-align:center;white-space:normal">ntent="t"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transparent;outline:0px">ntent="t"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transparent;outline:0px"> 论
清代的疆域和地理知识,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宏观山川脉络的认知。面对清代统治者发祥于中华传统文明核心区之外的政治现实,清初风水师遭遇解释困境,但受制于对东北地理的无知,并未提出有新意的山脉理论。康熙帝意识到新王朝与旧龙脉理论扞格不入,利用传教士以西洋新法进行大地测绘所得的地理新知,抛出“泰山源自长白山”的论断,试图将长白山塑造为单独发脉的另一座神山,并将中原文化的圣山泰山描述为长白山之余脉。在作为康熙朝大测绘最终成果的《皇舆全览图》部分版本中,绘制者画出南北两大干,意在构筑一种新的干龙走向,以取代传统的山脉论。
由于传统的强大惯性及地理知识增加,南北两大干未能普及,对康熙帝“泰山源自长白山”之说也不乏质疑。在对西藏和西域的测绘中,清朝官方将冈底斯山认定为天下山脉的中心,融合实测结果与佛教世界观,提出了新的天下山川脉络学说。从《大清一统志》到《西域图志》,这套学说逐渐丰富稳定。清中叶开始,关心西北史地的学者加入进来,他们大多强调帕米尔高原(葱岭)的中心地位,修补和完善官方山川脉络论,形成覆盖清朝广阔疆域的新型山脉学说。凭借出版活动与人际网络,有关边疆的地理新知广为传播。在这批学者笔下,以地理论证皇权的堪舆论调较少出现,以山脉系统配合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地理学色彩则在增加。特别是在边疆危机背景下,西域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以葱岭为天下诸山之祖的山脉论更催生出中国式地缘政治学。
不同于明代三大干龙局限于中国/王朝的地理范围之内,清代的山脉论还具有鲜明的世界性:印度诸山水(尤其是最具标志性的恒河)被认为源自冈底斯山,中亚、西亚乃至欧非诸山源于葱岭,俄罗斯诸山则源自阿尔泰山,至于东方的朝鲜、日本、琉球,乃至南面的缅甸、暹罗,无一例外也都在此系统中拥有位置。这种开阔的地理观念不但体现了清朝具有世界性特征,也强调了本国在更广阔山脉系统中的根本性位置。这两方面因素并存于晚清西北史地之学内部,并在近代国家转型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不过,精英阶层的知识累进和观念变革,未必会传导到一般社会的观念世界。弥补这个落差的是近代以来的地理教科书、边疆游记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传播活动。
中华文明与特定地理空间之间存在长久的互证关系。自《禹贡》《山海经》直到近代,有关中国山川脉络的探索与整理都是对文明空间持续不断的再确认与再适应。然而,对文明空间范围的理解,始终与国家疆域和王朝政治纠缠在一起,人间秩序特别是有关皇权的历史和传说影响甚至支配人们的地理观念。由于附加了文明、王朝、皇权等多重意义,有关宏观山川脉络的知识与理论在这方面尤为明显。近代以来,在教育层面,这套理论逐渐为地质学意义上的山脉学说所取代,不过传统的山脉理论及其世界观仍然部分存在于普通社会的地理观念之中,影响着人们关于世界、国家和权力的想象。
(作者段志强,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